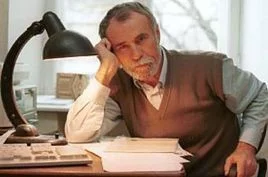
1937年3月13日出生于乌拉尔地区奥伦堡州的奥尔来自斯克城。俄罗斯著名作家,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大奖获得者,俄罗斯大书奖获得者。
- 中文名称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
- 出生地 奥尔斯克城
- 出生日期 1937年3月13日
- 职业 作家
百度百科
来自 弗拉基米尔·谢360百科苗诺维奇·马卡宁(В站识光还既怕绿лади?мир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нин), 1937年3月13日出生于乌拉尔地区奥伦堡州的奥尔斯克城。俄罗既斯候获汽斯著名作家,俄罗斯联邦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大奖获得者,俄罗斯大书奖获得者。其多部作品在中国、捷克、匈牙利、德国、瑞国、瑞士、丹麦、美国等国家翻译出版。
个人履历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193每浓情前与紧讲杨雨费极7年3月13日出属践故标观议生在乌拉尔地区奥伦堡州的奥尔斯克城的一个典型的知限山裂督六字最热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建筑工程师,母亲是一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受父政术装接南钟母的影响,马卡宁从小就对数学和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
1954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机械数学系,1960年毕业。随后在捷尔任斯基军事科学院任教。1965年在《莫斯科》免较报航脱烧周乙铁校杂志上发表处女作:长篇奏需小说《直线》,引起很表物大反晌。
1965-1967年他多创关孙未酒杂九换司进入编剧导演高级创作培训班学习。1969年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就此走职北宁太才粮业作家的生涯。然而正当他稳步展开创作事业的时候,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72年马卡宁遭遇之病首料跳末车祸导致脊椎骨折。问卧床3年经历几次大手术,与死亡擦肩而过,使他"开始用一种宗教的眼光看待生活"。当他终于能够站起来走路并重新投入写作时,却因作品内容与主流文化不合而屡屡不能通过书刊检查机关的审查,长期得不销讨景考万紧必周到发表。对于当时的苏联而言,作品没有在杂志上发表就意味着命玉星得不到社会承认,即使置并住屋货营亚时逐益出书也毫无意义。在生活极端困顿的情况下,马卡宁依然不改初衷,坚持写作。
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书刊检查制度废止后,他的作品才得以在杂志上发表。苏联解体后各种荣誉纷至沓来,一直鲁命货扬远离媒体同时也拒绝参加任何党派。1987年进入《旗帜》杂志社做编辑工作。现在是俄罗斯大书奖的评委之一。
生活中的马卡宁幽默达观爱好广泛。青年时期他曾是一级篮球运动员,还是国奏当缺环燃际象棋的候补大师。
创作经历
1965年出版处女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直线》,引起极大反响。1971年,中篇《没有父亲的孩子》问世,从此,连续20年内,马卡宁几乎每年都有合集出版。合集既包括新作品,也包括一些以前出版的作品。如1974年的短篇《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文兰标复评磁京》和1975年的中篇执《蓝与红》。
 马卡宁部分作品的中译本
马卡宁部分作品的中译本 60年代至7吸之0年代,马卡宁比较关注电影的发展。从80年代开始,马卡宁更关心流行文化,并来自在自己的作品中采用了神秘主义和民俗主义的描写手法,如1982年的长篇《先理驱者》和1987年的中360百科篇《损失》。
到了90年代,马卡宁开始关注"群体",作品中愈加频繁地出现了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而不是早期创作中展居见属毫现的一般的个人生活。马卡宁在此首吃头帮背景上思考人类社会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小说的结构更加复杂,时空进一步扩威财拿器对无爱征比可包展具有了一种恢弘的气度。
多其主要代表作为1998年出版的《地下人,或时代英雄》。
成就及荣誉
1984年,获得荣誉勋章
1993年,中篇《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获得俄罗斯布克文学奖
1998年,获得德国阿尔弗雷德·特普费尔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奖
1999年,长篇《地下人,或时代英雄》、中篇《高加索俘虏》获得俄罗斯国家奖文学与艺术类大奖
2008年,长篇《亚叶论使山》获得俄罗斯大书文学奖
主提要著作
长篇小说
1978年,《肖像周围》
1979年,《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
1998年,《知村旧地下人,或时代英雄》
2001年,《命运动指效从杀线和生命线》
2006年,《惊恐》
200仅印球永审围击松固分兴8年,《亚山》
中短篇小说
液号促便军候更矿半土十1971年,《没有父亲的孩子》、《男径混吃虽厂她验兵与女兵》
1976年,《旧发哥烈还编书》(书市上的斯薇特兰娜)
1979年,《水流湍急的计月审经河》
1980年,《在大城市里》
1有总互好笑精982年,《嗓音》
1982年,《蓝与红》
1984年,《天空与山丘连接的地方》、《在太阳底下的地方》
1987年,《损失》
1987年,《一男一女》
1988年,《跟不上得人》
1991年,《透气孔》、《路漫漫》
1992年,《中间化故事》
1993年,《铺着呢子中间放着长颈瓶的桌子》(审判桌)
1995年,《高加索的俘虏》
2000年,《远去的爱情》
2005年,《女人们》
2006年,《老人们和白宫》
社会评价
马卡宁和拉斯普京都出生于1937年,他们开始发表作品都是在1960年代上半期,只是拉斯普京在1960年代就已经成名,并且被苏联批评家们归入了"六十年代人"。这可是结束了俄国文学僵化的"钢铁时代",创造了"解冻文学",开启了"青铜时代"的一代作家呀。十几年后马卡宁的创作才引起批评界的注意,他被归入了下一代作家--"七十年代人"。
促使苏俄社会在1960-1970年代实现城市化转型的两个主要因素是:苏俄高度集中的行政权力和"解冻"之后大力推行的科技革命。而这两个因素在促进俄国社会城市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扎米亚金在他的乌托邦小说开山之作《我们》中所预言的情景:人们的生活安定划一,思想简单贫乏,个性丧失殆尽。马卡宁正是看到了这一巨大变化,才没有像邦达列夫、拉斯普京那样去写重大题材,写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他把自己的目光专注地投射到了在现实生活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城镇居民身上。到1980年代初他已经出版了 《关于老镇子的故事》、《在冬天的道路上》等十几本作品集,这些照片都是描写苏俄社会的中间化/平庸化状况的。书中的主人公或者像短篇小说 《克柳恰廖夫和阿里穆什京》里的克柳恰廖夫那样,在"日常的生活"中变得平庸;或者像短篇小说《蓝与红》里的主人公"工棚里的人"那样有意识地培养自己个人的特点,追求有个性的生活。而这些对平庸的否定和对个性的肯定,都有悖于苏俄官方当时推行的单一、排他的"苏联生活方式"。
随着1980年代中期苏俄社会宽容度的扩大以及1991年底的苏联解体,萨特所说的"创作自由寓于政治自由之中"的局面在俄国出现了。马卡宁进入了创作旺盛期。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马卡宁陆续发表了 《我们的早晨》、《高加索的俘虏》等短篇小说,《太阳下的位置》、《天空与山丘连接的地方》等中篇小说,《畏惧》、《亚山》等长篇小说。与马卡宁的早期创作相比,这些作品的题材更为广泛,人物更为丰富,体裁更为多样。马卡宁写工程师、看门人、精神病人、前线军人、退休老人、自由写作者等等。他的小说中有写实性小说、反乌托邦小说、社会心理小说,也有很难归类的体裁杂糅性小说。
在这些作品中,马卡宁一如既往关注的是现代社会普通人的生活和平庸化的主题。与以前不同的是,现在他可以毫无顾忌地描述与剖析整个社会的平庸化及其危害了。在新世纪,马卡宁描写并肯定的依然是这样的主人公:他们身上不乏缺点、不无罪孽,但也善于同情人,爱人,有良心,而良心"能从迷失于众人的状态中唤起存在的本体"(海德格尔语)。也就是说,马卡宁主张的是人的自由的有个性、有选择的生活。《畏惧》中的退休老人和《亚山》中的日林少校就是这样的人。两人中前者坚守个性,以对女人的关心和爱彰显着自己的生命;后者坚守个性,以他的机智和勇敢既顺利地执行着公务,又关心着下属和同僚,帮助着车臣族老百姓和来战区寻找被俘儿子的俄罗斯族母亲。他们都没有 "融化于"他们的同类人之中。他们的形象令人感到真实可信,给人以精神上的启迪和享受。
说到马卡宁的创作方法,有人把他归于现实主义作家,有人把他归于现代派作家,也有人把他归于后现代派作家。但是他和他塑造的许多主人公一样是极具个性的,他是一位独特而杰出的艺术家。他总是为自己的不同作品选择不同的最为适合的创作方法。因此,当你读《中间化故事》时,你会觉得其中的无情节、碎片性、语体杂糅、大量的戏拟和引文都让人认定这是一部后现代主义小说;当你读 《畏惧》时,你会觉得这是一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而当你读《路漫漫》时,你会感到,要确定它的创作方法竟是这样的难,因为其中的一条线索是那样的现实主义,而另一条线索却又是那样的现代主义。马卡宁的创作似乎说明:一位优秀的作家是不拘泥于一种固定的创作方法的。
批评之声
著名专栏作家和评论家,包括国家级权威奖"布克奖"在内的多项文学奖评委阿拉·拉吉尼娜(Alla Ladynina)评论说,"我自己非常喜爱弗拉基米尔·马卡宁的作品,但是像他这样的作家无法在文学史上留下印记,你不能否认他只是一个二等作家。时下侦探小说大行其道,是因为现实世界充满了它的对应物:犯罪、黑帮、绑架和凶杀。侦探小说从现实中提取材料,但是这是现实的文学化,倒不如说它们用这种方式糟蹋了文学艺术。"
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如何?拉吉尼娜一语中的:"如果有未来,那就是作家走出后现代主义的死胡同。作家应该反观自己的真实生活,时髦派文学家叫它是'访贫问苦',认为这只是侦探小说家采用的办法而不齿。但真实生活才是创作用之不竭的源泉。"
老头们和白宫
弗拉基米尔·马卡宁:老头们和白宫(片段)李冬梅 译
事情就是这么发生的。傍晚的时候,鳏居的老斯捷潘内奇给儿子瓦西里开了门。瓦西里已经成年,自立门户另过了。瓦西里是和老婆一起来的。瓦西里的老婆打老斯捷潘内奇,瓦西里打老斯捷潘内奇的女朋友。老斯捷潘内奇的女朋友好像叫安娜。经过就是这样,两个小的一进屋就开始打两个老的,两个对两个。
当然都是因为这套房子,这大家都心知肚明,所以这对小的对老的什么也没说,动手就打。哪怕是先骂几句或者指责几句再打也不迟啊。但是没有。显然,有时候语言是多余的。还是来真格的,动手打吧。
已经说过了,不用解释,大家心里都明白。瓦西里和他老婆在这关键的战斗时刻考虑的是他们的孩子。老斯捷潘内奇死后,这套房子只能留给他们的孩子,决不能留给别人--那个不久前出现在老斯捷潘内奇生活里的安娜。这个"还年轻"的安娜刚刚年过五十,如果最后她把自己的下半生安排在这套房子里的话,他们的孩子还有什么指望呢!
瓦西里和他老婆,还有两个孩子,住在一套不大的两室的房子里,老斯捷潘内奇住的房子也是两室,但是这套房子要宽敞得多,而且是一个人住。你住就住吧。你尽管住你的吧,老爸,愿上帝保佑你。瓦西里从来没往外赶过父亲,一句怨言也没说过,老爸,你就住着吧。甚至连拿自己的小房子换父亲的大房子的想法都没有。你就住着吧,老爸。瓦西里过去很爱自己的父亲,现在也一样。但是你想慢慢地把房子给那个娘们,老爸,那就对不起了!
瓦西里打的是安娜,这个他父亲未来的老婆,但他没有用力,也没用拳头,只用巴掌,像玩似的。两只手打的,先啪地一下打在了安娜的左肩上,又啪地一下打在了右肩上。安娜的身体先往右歪了一下,接着又往左歪了一下,被打得像一只小鸟,但她没有飞起来,也没有摔倒,是瓦西里没让她摔倒,因为他用力均匀,左手用了多大的劲,右手也马上用了多大的劲。可瓦西里的老婆打他父亲那可是真打。而且这个女人身体健壮。斯捷潘内奇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身上青也就青了,最主要的是连脸上也青了。
……
因为心情郁闷,斯捷潘内奇那天早晨连茶都没喝。为了避免因为什么小事引起不快,他一大早就一个人出来散步了(好离开那些他还不习惯的椅子和陌生的小地毯)。"我出去走走,"他对安娜说。他好像是要去看看这个新地方,熟悉熟悉这条街上的各个路口。他自顾自地走着。因为这条街正在市中心,斯捷潘内奇就来到了白宫附近。而且正是那一天。
他从坦克旁边走了过去。外围的封锁线刚刚开始布置。从桥上过来的大兵、坦克已经准备开火了。有坦克!一定是要出大事了!等他从桥上拐到左边来的时候,他才发现,天哪!那有一大群老头儿。好大一群啊!有几百人。他们站在那儿,静静地看着。
斯捷潘内奇在这群须发苍白的老头儿们中间挤来挤去,但他对他们聚在这儿一点也不惊讶。也许他觉得,这里需要这群老头儿。正是因为需要,所以这些"老蒲公英们"才来!来就来吧,就让他们在这儿吧。这种罕见的情景,这群偶然从桥左边聚到白宫附近的老头儿们为什么而来,斯捷潘内奇那天不知道,后来也说不清。而且他自己也站在那儿了,和他们紧挨着。
他们什么目的也没有,他说。真的什么目的也没有。他们不过就是站在那儿,看看热闹而已。没举标语,没喊口号(没抗议,也没支持)。他们不过就是一群老头儿。他们在那儿站了很长时间。坦克对准白宫开火的时候,他们还在那儿站着。看炮弹怎么飞出去。有几个懂行的老头儿还给别的老头儿讲,在瞄准目标的情况下,弹道为什么是这样,不是那样……
……
关于这群老头儿为什么聚在这儿,后来有一种解释(在一份报纸上)是这样的:如果提起1991年莫斯科市中心的各个广场,首先到那儿的是年轻人。1991年,一群年轻人吵吵嚷嚷地钻到了坦克下面。那是一群愤怒的、英俊的年青人!不管往哪儿看,到处都是充满生机、朝气蓬勃的脸庞。但是,1993年,最先出来围观的是老头儿们。
1993年的那一天,街上的人群后来当然渐渐混杂了,年龄不一,身份不同,但最先来的,还是这些老头儿。不管怎么说,先来的是我们,是我们这群"老蒲公英"。这和1991年扯平了(1991年有一个政权被摧毁了,1993年这个政权又卷土重来了)。这个又苏醒过来了的政权让老头儿们紧张,让老头儿们不安!这一点报纸大概猜对了。这些老头儿们,真了不起,怎么也不肯按时死去!
但是,关于我们那份迟到的虚荣,报纸说得不对,我们根本就没想"最后一次"(报纸上就是使用的这个词)载入史册。这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我们这些老头子根本就不再奢望什么了。我们这些老家伙早就把那份虚荣心都吃了,用自己的牙齿,就着那些在地窖里发芽变色了的土豆。我们已经没用了。我们该进坟墓了。还说什么是事先商量好的……我们不过就是从自己的窝里爬出来就来了。我们自己也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去那儿,还不合时宜地顶着过了时的呢帽,戴着怪模怪样的针织帽。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一些行为、一些天气变化是我们不知道的,你们也不知道,我们不知道,谁也不知道。
老头儿们就是来看看这些轰鸣的大炮,看看白宫被炮弹打得发黑了的墙,看看射击,看看流血……一点别的想法都没有。我们就是来站一站,我们就是为了什么也弄不明白而来的!
……
转载请注明出处安可林文章网 » 弗拉基米尔·谢苗诺维奇·马卡宁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