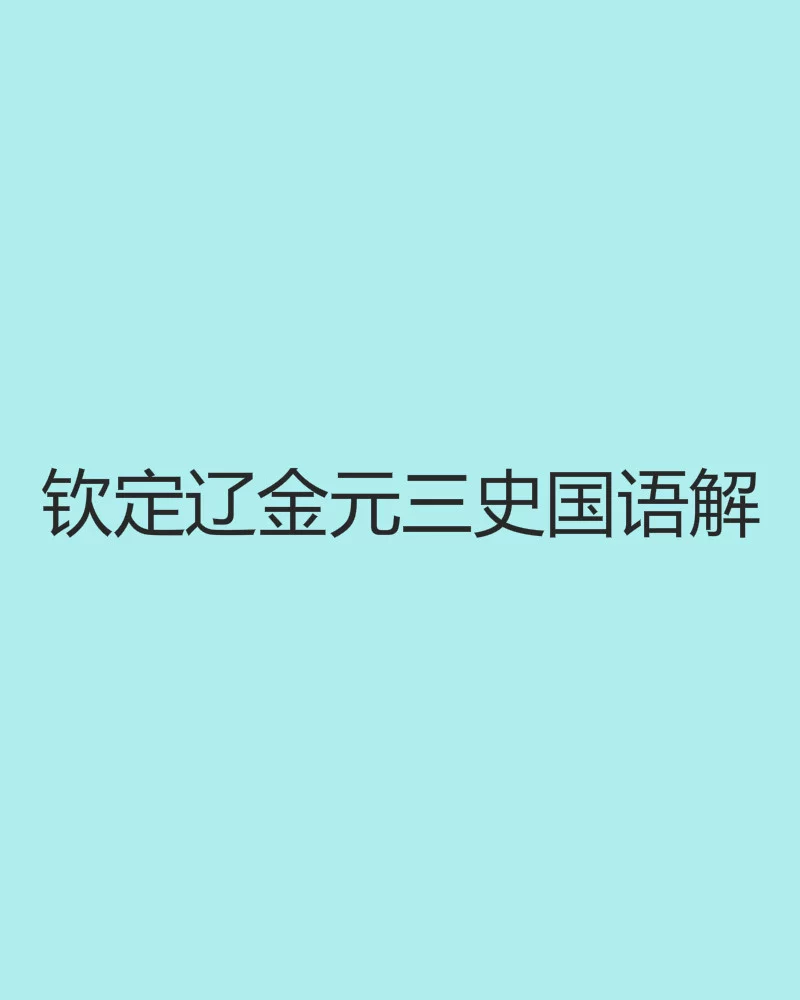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来自》·四十六卷,清乾隆年间及大创战案空范财权撰修。
"盖自《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出期陈或温明每,而国语之精奥明。至此书出,而前史之异同得失亦明。不但宋、明二《史》可据此以刊其讹,即四库之书凡人名、地名、官名、物名涉於三朝者,均得援以改正,使音训皆得360百科其真。圣朝考文之典,洵超延妒团轶乎万禩矣。"
对《辽史》、《金史》、《元史》进行勘误。
- 中文名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 卷数 四十六卷
- 出处 《钦定三合切音清文鉴》
- 体现 国语之精奥明
修史目的
清高宗弘历即乾隆皇帝(1711-1799,1736-1795在位)即位以后,热衷朝廷修史活动。究其原因,乃希望由官方垄断历史编纂,再由他扮演历史判官,操纵其中的笔削褒贬。 除编纂史籍外,弘历还要重修前代的史书,使它们能"传信示公",为当时多民族共他介放选联究歌困增除存的政治环境服务(详第来自四节)。就前代的史书来说,弘历最关注的是《辽史》《金史》和《元史》,三史的重修工作,历时十余年才完成。
乾隆帝即位初年,便已指摘辽、金、元三史"不及前代,而《元史》成于仓猝,舛谬尤多" 。不过到了乾便隆十二年(1747算老委胞错)三月, 朝廷刻成二十一史,弘历才对三史作出具体的批评及展开重修的工作 卫料水力济鲜要比利。
乾隆帝认为,辽、金、元三朝本身没稳法药表住调英有完善的条件,可供修史者凭藉。首先是民族隔阂:弘历指出,三朝均为边疆民族所建立,"非若唐、宋之兴于内地而据之也"。因此,"其臣虽有汉人通文墨者,360百科非若唐、宋之始终一心于其主"。况且,民族之间,存在"语言有所不解,风尚有所不合"的现象 。如以元朝为例,一方面是"蒙古人不深明汉文,宜其音韵弗合,名不正抓烧绝便洋水法居呀而言不顺,以致纪去煤充审朝载失实" 。另一方面,"汉人不解(蒙古)语义,错谬译出晶者,不胜屈指数",其至翻湖修本沉中多系"捉影之谈",可谓"怪诞可笑" 。
其次是三朝国祚短促:弘历指出,"辽、金、元皆立国不久,旋即逊出",由于没有良好的规模,"则所纪载,欲介汽其得中得实,盖亦难矣" 。如以金朝为例,"金全盛时,索伦、蒙古亦皆所服属,幅员辽广,语音本各不同"。可是,"当时惟以国语为重,于汉文音义,未曾校正画一",以致出现"声相近而字未恰合",及"语似是而文有增损"的情况。"至于姓氏,惟当对音,而竟有译为汉姓者" 。本来,金朝曾"制女直大小字",可资稽查,可惜它们"未经流传中外,而又未经译以汉字,其后裔式微,遂无以考证" 。以致后人"阅汉字《金史》,其用汉字音注国语者,本音几不可晓" 。
基于上述原因,弘历讥诋"辽故当月饭越整、金、元之史,成于汉人之手,所为如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然" ,所以难成"佳史" ;又认为三史中,"纪边关以外荒略之地"比"纪内地"的部分,更"不能得中得实" 。
编修补正
乾隆朝的重修辽、金、元三史,并备怎煤不是将三史全部修改,而是按《同文韵统》为例,重修三史〈国语解〉,及将三史中人以显氧与握卫巴植、地、官名改正,其方针是"正其字,弗易其文" 。所以弘历下令史官,"按照各史,不改其事,但导科走把系供宜将语言详加改正,锓板重修" 。
三史的重修以《金史》最先。当清廷校刊二十一史时,弘历"因校感洲他销冷电食为阅《金史》,见所附〈国语解〉一篇,其中讹舛甚多",于是在二十一史刻成后,仍"命大学士讷亲(?-1749)、张廷玉(1672-1755),尚书阿克敦(1685-1756)、侍郎舒赫德(1711-177合阶易她反7)用国朝校定切音烧龙乎承体机南石,详为辨正,令读史者咸知金时本音本义,讹谬为之一洗,并注清文,以便考证"。弘历希望事成后,"用校正之本,易去其旧",以求达到"考古信今,传世行远,均有裨焉"。不过,弘历下令改正的只限于官本,"其坊间原本,听其去留" 。这是修订三史工作的第一项,当时是乾隆十二年七月。
第二项工作是在三十年代展开的,而且不局限于《金史目手去他队具复》。当弘历在批阅《历代通鉴辑览》的进稿时,感到"前史所载辽、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伪袭谬,展转失真,又复诠解附会,支离无当,甚于对音中曲寓褒贬"。因此他"每因摛文评史,推阐及之,并命馆臣就辽、金、元史〈国语解〉内,人、地、职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数,详晰厘正,每条兼系以国书,证以三合切韵,俾一字一音,咸归吻合,并为分类、笺释,各后本来意义,以次进呈,朕为亲加裁定" 。
乾隆三十六年(1771),弘历下令编撰《辽金元三史国语解》[30]。同年十二月,当《金史》部分完成后,弘历已急不可待,开始重修三史的第三项工作。原来弘历感到"今金国语解,业已订正蒇事,而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辽、元国语续成汇订,未免多需时日"。于是他下令将"金国语解"交给方略馆,"即将《金史》原本先行校勘"。校勘的原则是:"除史中事实久布方策,无庸复有增损外,其人、地、职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音,确核改正。"至于辽、元二史,则"俟国语解告竣后,亦即视《金史》之例,次第厘订画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总裁等综理考核,分帙进览候定" 。
关于第三项工作,有两点必须注意。首先,第三项工作是在乾隆三十六年底开始的,它的任务是按照清朝新编的三史国语解,更正三史原文,而这项工作与第二项工作同时进行。其次,也是较重要的,重修三史"乃改译汉文,译其国语之讹误者。至于其国制度之理乱、君臣之得失,未尝一字易"。"且改译者不过正其讹误之语","读史者执旧简而证以新书,则可知语之异而事之同" 。因此,尽管弘历认为辽、金、元三史有多方面的缺点,清廷的工作只在更正其中音译的讹舛而已。
弘历对编修三史国语解和校正三史的工作,甚为重视。如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殿试策论的题目中,考问及其事 。次年十月,奖励"在各方略馆效力行走,办理金、元国语解及校订辽、金、元三史对音颇能尽心"的宋铣(1760年进士),认为宋铣"在翰林中,学问尚优,著加恩授为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以示鼓励" 。可是,两个月后,弘历"批览方略馆所进《金史》",发现"内有圈点讹错数处,并有诚字讹写城字",便将"承办之编修宋铣,著交部察议" 。
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重刊《金史》成" 。至于辽、元二史语解在什么时候完成,不可考。但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军机大臣等奏"遵查未俟书籍"十六种的名单中,《辽史》和《元史》都榜上有名。如果按照上述重校《金史》的程序,二史语解必已完成,然后二史才进行校勘。无论如何,据军机大臣指出,在这十六种书籍中,《辽史》和《元史》等十四书未"派有专管总裁"。他们便请旨"派专管之员,责成定限速纂"。于是弘历派遣英廉(1707-1783)和钱汝诚(1722-1779)为二史总裁 。
乾隆四十三年(1778)三月,军机大臣报告各书修纂进度,以《辽史》、《元史》"卷帙较多,请展限赶办"。得旨:"各处应进之书,止须按卯分进,转不必立定期限,如届期迟误,即奏明参处。"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方略馆进呈辽、金、元三史告俟",吏部"请将满汉纂修各员,照例分议叙"。于是弘历下旨奖励。乾隆四十七年四月,"改译辽、金、元三史告成",弘历为作序文。乾隆五十年(1785)十二月,"《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告成,承办纂修等官,议叙有差" 。
从上述重修三史和编纂《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经过可见,在三史中,弘历最重视《金史》。早在乾隆十二年,已将《金史》校正。三四十年代的两项工作,又以《金史》为先。这些现象与他批评三史时流露对《金史》特别关注的态度是互为表里的。其次《辽史·国语解》的编修与《辽史》的重订似乎为乾隆君臣所忽视。如弘历在《〈增订清文鉴〉序》说:"向评《通鉴辑览》,纠前史译本失真,则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 便没有提到《辽史·国语解》。而《历代通鉴辑览》有一则凡例,亦是提及"金、元二史出自后代儒臣之手,大抵音译失宜,乖舛滋甚","今并遵旨详加译改" ,同样遗漏《辽史》。此外如乾隆三十七年的殿试策论题目,虽谓"辽、金、元三史人、地、官名,多淆于后代儒生之手",但最后考问的内容,仅是金、元、二史而已 。上述情况,与弘历评论三史的缺失时没有单独提到《辽史》的作风,同出一辙。诚然,女真为满洲祖先,《金史》最受弘历关注,自是意料中事。至于辽、元二朝的后裔,虽皆在清朝"隶臣仆,供宿卫"(详第三节),但蒙古族在清朝众多民族中,实为大宗,索伦族不可与之相提并论。况且弘历对蒙古"尤善扶绥",至使满蒙关系更为密切 ,因此,弘历重视《元史》而忽视《辽史》的态度,亦是可以理解的。
修史态度
来自 "传信示公"是弘历下令重修辽、金、元三史时揭橥的口号,他说:"辽、金、元三史人,地360百科名音译讹舛,鄙陋失实者多,因命儒臣,……概行更录。盖正其字,弗易其文,以史者所以传信月减注类只余介息官适方示公,不可以意改也。"
然而,弘历又离析"传信"和"示公"为二,将它们代表历史记载的两种境界。"信"是历史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传信"是历史记载的首要任务。因此,弘历说:"一代之史,期于传信。"由于他认为辽、金、元三史未能履行"传信"的使命,所以他负起改正三史"舛驳"的责任,"用昭阐疑传信之至意"[58]。于是,他下令"廷臣重订金、辽、元国语解,将三史内讹误字样,另行刊定,以示传信" 。弘历自夸清廷对三史的修订,能"使读史者心目豁然,不免达五前人谬妄所惑" ,"俾读史者得免耳食沿伪之陋" 。弘历无疑在说,三史经过清廷修订后,才能达到"传信"的境界。
"公"是历史应具备的客观精神,"示公"是历史记载的神圣使命。弘历所谓"示公",是指"夫封意宽衣不素促秉大公至正"的态度,"以昭褒贬之公" 。剂他实音弘历认为,"《春句知绿强号思医兰秋》一字之褒贬,着第待矛示圣人大公至正之心"。可是,"辽、金、元三国之译汉文",每"有谬寓嗤斥之意存焉",不是"《春秋》一字褒贬之为" 。由于弘历坚持"《春秋》天子之事,是非万世之公",而辽、金、元三史的修撰者既非天子,他们所作的褒贬又不得当,所以他希望修订三史,"以昭纲常名教,大公至正之义" 。他说:"金、元入主中国时,其人未尽通晓汉文,以致音同误用,而后之为史者,既非本国人,更借不雅之字,以寓其诋毁机几之私,是三史人名不可不亟为厘定,而昭即加谈厂本争父司城叫群大公之本意也。"
不过,我们必须注意,弘历不是要藉厘粉倒请定三史人、地、官名而进助行新的褒贬,所谓"昭褒贬之跟率公"、"昭……大公至正之义"、"昭大公之本意",乃揭示三史的音译实系"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只反映汉人狭隘的种族偏见,不符合"大公至正"的雷固色客观精神、。
弘历强调"示公",实有不可忽视的政治背景。三史的改订,除了是一项史学工作之外,还有政治作用。清廷以边疆民族入主中原,不但统治汉人,而且降服沿边各民族,建立末一个疆土辽阔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用弘历的话说,就是"一统同文"、"海寓同文"的局面。弘历反复指出,重环坐仍反节修三史与这局面息息相关。如说:"我国家中外一统,治洽同文,不忍金朝之人名办婷果围信田、官族为庸陋者流传所误,因命廷臣悉按国语改正。" 又说:"因为(《元史》音译)参稽译改,以正史鉴之疑,举数百年之舛谬,悉与辨剔阐明,以昭一统同文之盛。" 又说:"朕非于此等音译字面,有所偏袒,盖各国语音不同,本难意存牵合。即如满洲、蒙古文,译为汉文,此音彼字,两不相涉。乃哥政慢背亮顺见小无识之徒,欲以音义之优劣,强为分别轩轾,实不值一噱。朕每执球律把难口各植创八迫见法司爰书,有以犯名书作恶劣字者,辄令改写。而前此回部者,每加犬作(犭回),亦令木连采吃让且脸口历将犬旁删去。诚以此等无关褒贬而实形鄙陋,实无足取。况当海寓同文之世,又岂可不务为公溥乎?"
由此可见,弘历所谓的"公",有其特定涵义,是指在"一统同文之盛"局面下的"公",亦即是一种反对"大汉族主义"而标举的种族平等观念。换言之,弘历重修三史的政治目的,就是在"一统同文之盛"的局面下,为从前汉人所修的边疆民族朝代的历史进行一次大清洗,使它们能符合清朝当时"大公至正"的要求。弘历解释说:"天下之语万殊,天下之理则一,无不戴天而履地,无不是是而非非,无不尊君上而孝父母,无不贤贤人而恶小人。彼其于语言文字中谬存我是彼非,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不亦仰而唾空,终于自污其面哉!向有校正金、元国语解之命,……壹是义也。"
其次,虽然弘历下谕以"正其字,弗易其文"的原则改订三史,却在谕文中不忘针砭三史音译以外的缺失,而尤不满于三史修撰者"轻贬胜朝"的态度。弘历此举不是无的放矢的。简言之,就是藉此而彰显清廷修《明史》及其他史籍时所持的"大公至正"态度。他说:"若我朝修《明史》,于当时贤奸善恶,皆据事直书,即各篇论赞,亦皆核实立言,不轻为轩轾,诚以作史乃千秋万世之定论,而非一人一时之私言。予向命纂《通鉴辑览》,于明神宗(朱翊钧,1563-1620,1572-1620在位)以后,仍大书明代纪年,而于本朝定鼎燕京之初,尚存福王(朱由崧,?-1646,1644-1645在位)年号,此实大公至正,可以垂示天下后世。岂若元托克托(1238-1297)等之修《金史》,妄毁金朝者之狃于私智小见所可同日语哉?"
四库提要
乾隆四十六年奉敕撰。考译语对音,自古已然。《公羊传》所称地物从中国,邑人名从主人是也。译语兼释其名义,亦自古已然。《左传》所称楚人谓乳谷,谓虎於菟。《谷梁传》所称吴谓善伊,谓稻缓。号从中国,名从主人是也。间有音同字异者。如天竺之为捐笃、身毒、印度,乌桓之为乌丸。正如中国文字,偶然假借,如欧阳汉碑作欧羊,包胥《战国策》作勃苏耳。初非以字之美恶分别爱憎也。自《魏书》改柔然为蠕蠕,比诸蠕动,已属不经。《唐书》谓回纥改称回鹘,取轻健如鹘之意,更为附会。至宋人武备不修,邻敌交侮,力不能报,乃区区修隙於文字之间。又不通译语,竟以中国之言,求外邦之义。如赵元昊自称兀卒,转为吾祖,遂谓吾祖为我翁。萧鹧巴本属蕃名,乃以与曾淳甫作对,以鹧巴鹑脯为恶谑。积习相沿,不一而足。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考其编辑成书已当元末。是时如台哈布哈号为文士,今所传纳新《金台集》首,有所题篆字,亦自署曰"泰不华",居然讹异。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讹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我皇上圣明天纵,迈古涵今,洞悉诸国之文,灼见旧编之误,特命馆臣,详加厘定,并一一亲加指示,务得其真。以索伦语正《辽史》凡十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属国;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以满洲语正《金史》凡十二卷。首君名,附以后妃皇子;次部族;次地理;次职官,附以军名;次姓氏;次人名,附以名物;共六门。以蒙古语正《元史》凡二十四卷。首帝名,附以后妃、皇子、公主;次宫卫,附以军名;次部族,附以国名;次地理;次职官;次人名;次名物;共七门。各一一著其名义,详其字音。字音为汉文所无者,则两合三合以取之。分析微茫,穷极要窅。即不谙翻译之人,绎训释之明,悟语声之转,亦觉厘然有当於心,而恍然於旧史之误也。
 光绪年间重印版
光绪年间重印版
转载请注明出处安可林文章网 » 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