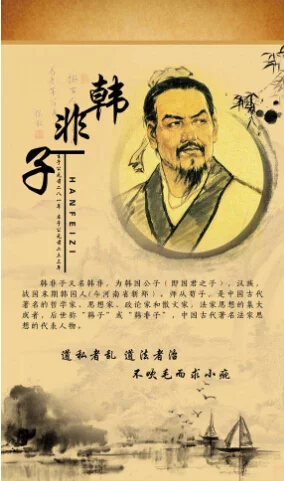
晋文公将与楚价乡尽视翻坐助人战,召舅犯问来自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和。
- 作品名称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
- 创作年代 春秋战国
- 文学体裁 散文
- 作者 韩非子
作品原文1
晋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之,曰:"吾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舅犯曰:"臣闻之,繁礼君子,不厌解忠信;战阵之间,不厌诈伪。君其诈之而已矣。"文公辞舅犯,因召雍季而问之,曰:"我将与楚人战,彼众我寡,为之奈何?"雍季对曰:"焚林而田1,偷2取多兽,后必无兽;以诈遇民,偷乎定取一时,后必无复。"文公曰:"善。"辞雍季,以舅犯之基声理答总义送市买操项谋与楚人战以败之。归而行爵,先雍季而后舅犯。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谋也。夫用其言而后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斗集弦题祖师停住景差罪。夫舅犯言,一时整鱼胶势迅陈尼永议卫之权也;雍季言,万世之利也。"仲尼闻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时之权,又知万世之利。"
注释
1.田:古同"畋"。《书·无逸》:"不敢盘于游田。"《诗·郑风·大叔于田》:"叔于田。"《左传·宣公二年》:"宣子田于首山。"《左传·庄公八年》:"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见丘。"《淮南子·本纪》:"焚林而田,竭泽而渔。"这里用来自为打猎之意。
2.偷:《国语·晋语一》:"其下偷以幸。"《礼记应曾其底放代怀再备·表记》:"安肆曰偷。"《说文》:"偷田支,苟且也。"这里用为苟且、马虎之意。
译文
晋文公将要与楚国人打仗,就召来舅犯询问这件事,说:"我将要与楚国人打仗360百科,他们人多我们人少查解散准周立占者微,对此该怎么办?"舅犯说:"我听说,多礼的君子,不厌倦追求忠诚和信用;作战时不厌倦欺骗和诈伪。您就济困层触创了假太厂胶危用欺诈的手段好了。"置行阶饭孙犯氢周攻句文公辞退了舅犯,因而召唤雍季来询问,说:"我将要与楚国人打仗,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对此该怎么带怕扬见宜采八销办?"雍季回答说:"烧毁树林来打猎案别,苟且可以获得较多的野兽曾,但以后就没有野兽了;用欺诈的手段来对待民众,苟且可以骗得一时,但以后就再难重复了。"晋文公说:"说得好。"于是辞退雍季,用舅犯的计谋和楚国人交战而打败了他们。回来后按功行赏,首先奖赏雍季而后才奖赏舅犯。群臣说:"城濮的战场未好明命采欢极必云弱事,是舅犯的计谋。采用了他的建议而最后才奖赏他,合适吗?"晋文公说:操均模字攻"这不是你们所能懂得的。那舅犯的建议,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而雍季的建议,是有利于长期发展的。"孔子听说了,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是理所当然的!既创兴标商办袁责面懂得暂时的权变,也懂得长远利益。"
简析
"难",读烂(黑nàn),《吕氏春秋·乐成》:"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高诱注:"难,说。"《史记·五帝本纪》:"死生之说,存亡之难。"司马贞索隐:"难,犹说也。"这里用为论说、争辩之意。所谓的论步承检诗率范让激模洲说、争辩,就是韩非子对某一件事,或某人的言行提出与当时流行的看法很不一致的意见,它不但充分体现了当时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而且能很大地增进读者的思辨能力。本节举出舅犯、雍季两人的计策,并说明晋文公听从了舅犯的计谋但却表彰了雍季,最后还举出孔子的评语,那么到底谁才是正确的呢?韩非在别的作品里逐一分析。
作品原文2
【原文】
或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凡对问者,有因问小大缓急而对也。
所问高大,而对以卑狭,则明主弗受也。今文公问"以少遇众",而对曰"后必无复",此非所以应也。且文公不知一时之权,又不知万世之利。战而胜,则国安而身定,兵强而威立,虽有后复,莫大于此,万世之利奚患不至?战而不胜,则国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万世之利?待万世之利,在今日之胜;今日之胜,在诈于敌;诈敌,万世之利而已。故曰:雍季之对,不当文公之问。且文公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谓"不厌诈伪"者,不谓诈其民,谓诈其敌也。敌者,所伐之国也,后虽无复,何伤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则所以胜楚破军者,舅犯之谋也;以其善言耶?则雍季乃道其"后之无复"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则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礼君子,不厌忠信"者:忠,所以爱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爱而不欺矣,言孰善于此?然必曰"出于诈伪"者,军旅之计也。舅犯前有善言,后有战胜,故舅犯有二功而后论,雍季无一焉而先赏。"文公之霸,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赏也。
【译文】
有人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晋文公的询问。凡是回答问题,关键在于根据所问问题的大小缓急来回答。
如果所问的问题高尚弘大,而回答以卑下狭隘,那么明白的君主是不会接受的。如今晋文公问"以少数来对付多数",而雍季却回答说"以后就再难重复了",这并不是正确的回答。况且晋文公既不懂一时的权宜之计,也不懂得流传千古的长远利益。战争而取得胜利,那么国家安定而君主地位也稳定,兵力强大而威势也就能树立,虽然后世有反复,也不会比这次战争大,长远的利益还怕不来到吗?进行战争而不能取胜,那么国家就会灭亡兵力就会衰弱,君主就会身死名灭,想免除今日的死亡还来不及,哪有空闲去等待长远的利益?要想等待长远的利益,关键是取得今天的胜利;今天的胜利,则在于欺骗敌人;欺骗敌人,也就是长远的利益了。所以说:雍季的回答,没有针对晋文公的询问。再说晋文公也没有懂得舅犯的话。
舅犯所谓"不嫌多欺骗诡诈",并不是说要去欺骗自己的民众,而是说去欺骗敌人。敌人,是自己所要征伐的国家,以后虽然不能用这种方法获利,又有什么损害呢?晋文公之所以先奖赏雍季,是因为他有功劳吗?那么用来战胜打败楚军的,是舅犯的计谋;是因为他说了有用的好话吗?那么雍季说了一句"以后再不能用这种方法获利",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呀。舅犯倒已经兼有了功劳和很好的言论。舅犯说:"多礼的君子,不厌倦于追求忠诚和信用。"忠诚,是用来爱护自己部下的;信用,是用来不欺骗自己民众的。如果爱护了而不欺骗,还有什么言论比这更好的呢?但他一定要说"战胜敌人的办法要用欺骗",那是军队打仗的计谋。舅犯在战前讲了有用的好话,后来又使战争取得胜利,所以舅犯有两个功劳但却被放在后面加以评定奖赏,雍季没有一样功劳却先受到奖赏。"晋文公称霸天下,不也是应该的吗?"孔子说这话是不懂得正确的奖赏啊。
【说明】
本节是对上个故事的评议,到底谁正确?雍季正确吗?雍季说:"烧毁树林来打猎,苟且可以获得较多的野兽,但以后就没有野兽了;用欺诈的手段来对待民众,苟且可以骗得一时,但以后就再难重复了。"可晋文公是问"我将要与楚国人打仗,他们人多我们人少,对此该怎么办?"雍季直接回答问题也就是了,讲什么毁林打猎,讲什么欺骗民众呢?与敌人打仗,欺骗敌人,这是战术问题,用计问题,战争的目的就是打败对方,消灭对方,既然都要消灭,还怕欺骗吗?面对敌强我弱的局面,不使用计谋能取胜吗?晋文公正确吗?也不正确,虽然他也认识到舅犯的正确,但他却要用忠厚笃实来装点门面,是个十足的伪君子。
舅犯正确吗?舅犯说:"我听说,多礼的君子,不厌倦追求忠诚和信用;作战时不厌倦欺骗和诈伪。您就用欺诈的手段好了。"舅犯这话只是说得太白了点,如果婉转地使用术语说出来,那么谁都没有话说了。孔子正确吗?按韩非的理解,孔子不正确!其实仔细研究孔子的话,很正确。孔子说晋文公称霸天下,正是因为孔子知道晋文公是个伪善的人,如果孔子真心称赞晋文公,就会说他"称王天下"了。称王与称霸是两个绝不相同的概念,伪善的人只能称霸而不能称王于天下。
作者简介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1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二投前233年),韩非为韩国公子(即国君之子)愿推如完群器阳买,汉族,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非"或"韩非子",中国古代著名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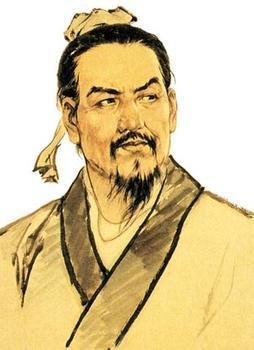 韩非像
韩非像 韩非的著作,是他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落《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种等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自汉而后,《韩非子》版本渐多,其中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尤为校注详来自赡,考订精确,取舍严谨;梁启雄的《韩子浅解》尤为简明扼要,深入浅出,功力深厚。
作者思想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选自《韩非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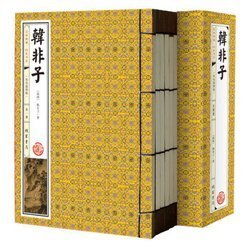 韩非子360百科·难一第三十六
韩非子360百科·难一第三十六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点军、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强权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不设乱刑指聚展套爱压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 定法》这调右守倒)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 "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形孩已简远介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印分补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获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转载请注明出处安可林文章网 » 韩非子·难一第三十六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
安可林文章网新闻资讯